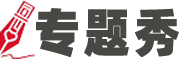變老的方式 | 香港:全球最長壽地區,養老并不容易
誰來養老
長期以來,香港以“自力更生”、“效率優先”的理念主導著社會福利政策的走向,選擇市場為主、政府補助為輔的退休保障制度。現有的養老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由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和“綜援” (類似內地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組成,資金由政府財政統一支出。高齡津貼為每月1345港元,針對70歲及以上的老人。綜援申領的要求較多,對老人的資產和身體狀況都要進行整體評估,最貧困和護理需求最高的老人每月可領取5930港元,而身體欠佳的老人可領取每月3485港元的補助。但這相對香港的物價來說只是杯水車薪,單純依靠政府的援助津貼很容易陷入晚年貧窮的境地。
養老金的第二大“支柱”統稱為“職業儲蓄”,也就是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這是香港的兩大資金積累型的養老金體系,也是香港養老金制度的核心。顧名思義,強積金帶有強制色彩,任何18至65歲在職人士都必須參加強積金計劃。標準為雇員每月收入的10%,其中5%由雇員繳納,另外5%由雇主繳納,自雇人士供款標準為其收入的5%。雇員可自行選擇投資計劃,至65歲法定退休年齡時,雇員可一次性將累計收益及多年來累積投入的本金一次性取出。強積金制度從2000年起已施行十余年,參與率很高,但也不斷遭各方詬病。環球股市大起大落,投資回報甚微,上班族還要繳納不菲的基金管理費,根本無法指望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可以取出多少養老錢。
第三“支柱”是“個人儲蓄及家庭資助”。香港市場上有豐富的養老投資理財產品,在職人士擁有多種選擇為自己的養老投資。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投資產品開發得尤其充分,保險類投資產品的選擇也比內地多, 對于高凈值人士和投資者來說不僅保障性高,回報也比較可觀。
在個人高收益的保障下,香港老年人壽命全球稱冠。“有產”的香港老年人可以享受高效而低價的公共醫療體系,既有世界一流的醫術,又有豐富完善的香港醫療保險計劃減輕大病負擔,還有菲傭解決照護需求,香港獨具特色的飲食養生也功不可沒。社會集體追求長壽,也催生了民眾更強的健康意識。很多老年人每天早上會在這座城市的安靜角落進行鍛煉,這也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延長壽命。
但是,香港現有的養老制度還遠遠算不上是全民退休保障。在實行該制度前已經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無法受惠;家庭主婦、殘疾病患等沒有正式工作的社會弱勢群體,由于沒有向強積金賬戶供款,老來就沒有保障。而香港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實質進一步惡化了這部分老人晚年境遇。香港經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歷了重大變革。當時,大部分在五六十年代促使香港成名的制造業活動都移至中國內地,取而代之的是銀行業、保險業、物流及房地產業,這些服務行業目前雇傭了將近90%的勞動力。高技能勞動力的養老保障比較完善,而許多教育水平較低的工人則是全然不同的境況。對于沒有技能或技能不足的人來說,香港是一個艱苦的地方。
在這座繁華喧鬧的城市里,不難見到兩鬢花白的老人在餐廳、超市、商場、辦公樓里面做著最低等的工作:收銀、抹臺、掃地、刷碗、清潔廁所。年過六十、辛苦了一輩子仍不能坐下來喘口氣、享受兒孫繞膝之樂,反而和年輕人一樣,早出晚歸,為著兩餐一宿奔命,不敢懈怠。
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全港市民都獲得福利,近年來也有不少人或組織提出建議方案,例如年滿65歲老人,單身資產不多于8萬港元、夫婦兩人資產不多于12.5萬港元,每人可每月領取3230元退休金,預計25萬人受惠。而這個方案遭到了年輕人的激烈反對,他們擔心這樣一來會大大增加年輕一代的負擔。據測算,這個方案到2064年累計新增開支總額為2555億元,會令政府提早6年出現結構性赤字,財政儲備提早8年耗盡。彼時,“社會掉入泥沼,不能自拔。”
一床難求
香港人口急速老化,老人患病、殘疾比例也有所增加。據統計,2013年60歲及以上人士中,61.8%患有至少1種慢性疾病,28.4%至少有一項殘疾。這些老人中,又有60%是獨居老人,缺乏親人照顧,獨居有一定危險。但是,香港安老服務長期存在供給不足問題。香港2017年有6259名老人在輪候期間離世,人數創過去5年新高。至2018年5月,仍有3.8萬名老人正在輪候政府資助床位。
隨著老人護理需求增長,香港社會福利署自2000年起推出“養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符合資格的老人可以申請政府資助床位,包括公營性質的養老院(津助或合約養老院)床位,以及政府在私營性質的養老院購買的床位。但是,因為興建院舍耗時長(一般最少需要5年)、業界人手短缺等問題,從2010至2011年度到2014至2015年度,輪候資助床位的老人增加了4598名,資助名額只增加了1457個;床位輪候時間也十分漫長,在2014至2015年度,入住公立養老院平均需輪候37個月,入住私營養老院的資助床位也需8個月。
除資助床位外,老人也可入住沒有參與政府買位計劃的私營養老院,但這些養老院只達到《養老院條例》規定的最低標準,缺乏監管、問題頻生。有報告顯示,這些養老院的住客人均面積為7.5平方米,每百名住客僅配有16.3名員工(包括護士、保健員、護理員等),與合約養老的20.8平方米、42.3人有顯著差距。私營養老院也多次傳出虐待老人的丑聞,如一家位于高樓內的重度護理養老院,將12名失去自理能力、坐在輪椅上的女性老人推到三樓露臺,老人被迫脫光衣服等待洗澡,一等就兩個小時。
為了緩解床位短缺的難題,香港政府近年開始推行老人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計劃,目標對象為在中央輪候冊中身體機能被評為“中度缺損”的老人,香港所有甲一級標準的安老院舍,皆可申請成為認可服務機構。院舍券試驗計劃原定于2015年9月推行,但隨即發生大埔劍橋護老院涉嫌虐老事件,令人質疑私營安老院的服務質量以及政府監管能力。其后2016年3月,該計劃再度實施,不過9月將計劃范圍擴大至所有甲一級安老院后,監管系統再度失守。社會輿論批評 “服務券” 計劃是將安老的責任市場化、商品化,老人未必能夠真正受惠。
香港養老模式。
由于日趨沉重的財政壓力和被照顧的老年人精神問題頻出,香港的養老模式開始逐漸向社區養老轉變。社區養老融合了傳統家庭養老和集中院舍養老的優勢,更加關注對老年人的心理情感關懷。社會福利署直接向社區養老服務機構提供資助,透過資助服務機構、援助困難老人,調控收費標準,改善老人養老處境。
“出口老人計劃”
面對著四萬名排隊等待補貼型養老服務的老人,壓力之下的香港政府正在尋求廣東省和福建省的養老合作,這也可能成為其解決長遠人口問題的方案的一部分。這與內地產婦去香港生娃、內地各年齡段的孩子去香港讀書形成了鮮明對比。
自2013年起,香港政府開始了一種新奇而獨特的養老嘗試——“廣東計劃” 和“福建計劃”,為選擇移居廣東省或福建省、符合申請資格的年老人每月發放“高齡津貼”,金額達1290元,另外豁免已經移居廣東省、符合申請資格的老人須在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至少一年的規定。計劃實施后,先后有將近兩萬高齡香港老人回到內地養老,大多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從內地到香港謀生的老人。
內地廣闊的空間可以幫助消化香港難以承受的老齡化壓力。不少香港老人對去內地生活持積極態度,尤其是那些在內地有親戚的老人,他們認為內地的養老院環境不錯,也適于居住。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不可能像內地養老院這樣為每位老人提供一個獨立房間。另外,香港普通家庭居住面積過小,所謂的公寓也十分狹窄,一家人擠在一起,居家養老也捉襟見肘。搬到內地,居住環境會得到很大改善。
不過有不少老人對此沒有興趣,很多老人已經等待政府養老床位4年,不愿意放棄機會。另外,很多老人不愿意返回內地養老,因為在家中仍承擔照料的任務,沒有辦法離開一直臥床在家、無法自理的伴侶。有些老人覺得家人前來探望不像在香港那么方便,老無所依非常孤獨,他們更愿意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
內地物價上漲也是促使老人返港的一大因素。不少香港人當初選擇到內地養老時,都帶著相對豐厚的積蓄,懷揣著“內地物價低、港幣值錢、空氣好、住房寬敞”的頤養天年夢。但是,近幾年隨著人民幣升值、內地房價物價上漲,環境問題凸顯,一些內地港人年邁體弱多病,生活日益拮據,無奈之下選擇踏上返港之路。
除了情感、經濟和文化傳統的障礙,香港政府的“出口老人計劃”似乎還有個制度問題:一旦離開香港,就無法享受香港老人的許多福利。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市民能得到的政府津貼有限,而無論內地政府還是香港政府都沒有向此類人士提供醫療福利。雖然香港公立醫院要排隊看病,但每人住院只需100元/天的福利還是讓老人家安心,所以退休后去內地養老的香港人經常回到香港接受治療。
針對這種現狀,香港政府也增加對移居內地老人的支援,2015年,香港政府推出醫療券試點計劃,返鄉老人可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每年2500港元的醫療券。香港賽馬會和NGO合作在深圳和肇興設立了養老院,專門服務香港返鄉老人。這兩家養老院均提供醫療顧問服務,并為那些需要在上水北區醫院接受后續治療的老人提供交通服務。
有沒有一個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的養老問題?答案當然是沒有。不過,這并不妨礙人們不停地探索。香港,作為全世界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一直是積極的探索者。而爭論從未間斷,演變也尚在進行。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均為采集網絡資源。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可聯系本站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