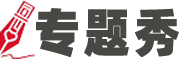中醫經典文獻里的“精氣神”

從我國最早的中醫理論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到漢代名醫張仲景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再到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醫典籍世界浩如煙海,凝結著幾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醫學智慧。
如何海量歸類,如何優中取精,又如何讓那些躺在古老典籍中的文字,隔著遙遠的時空,為今天的每一位中醫從業者所用,甚至發揮、創造出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30多年來埋首于中醫文獻整理與研究的何清湖,正是在堅持走這樣一條路。
沿著何清湖的足跡,人們也能看到一個關于中醫藥傳承與發展的時代之問——中醫藥的底氣與自信,究竟從何而來?以這些經典文獻為載體,它從傳統中來,正在往現代乃至更新的未來走去。
“不可能”的任務:
《傳世藏書(子庫·醫部)》
據《中國當代出版史料》記載,1949-1951年期間,醫藥古籍僅整理出版過20種。那是一個百廢待興,經濟力量卻又相對薄弱的時期,中醫藥在此后幾十年間,都在等待一個厚積薄發的時刻。
1982年,衛生部中醫司在北京召開了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工作座談會,初步擬定了《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年》,這標志著中醫古籍的整理與出版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被納入國家層面的規劃實施中。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古籍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 1991年—1995年—2000年)》的大背景下,海南出版社申報了國家重點文化項目“傳世藏書”。這是一套囊括我國從先秦到晚清歷代重要典籍的大型叢書,由中國學界泰斗季羨林教授擔任總編,是繼《四庫全書》后兩百年來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其中的《子庫·醫部》部分,找到了當時正在準備赴上海攻讀博士學位的何清湖擔任主編。“這確實是一次冒險,畢竟當時我還只有二十幾歲。”
在此之前,出身于中醫文獻方向專業的何清湖,已經參與過國家兩大文獻整理項目:《中醫方劑大辭典》,以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直接主持的重大科研課題《中華本草》。但“參與”和“主編”之間,還是存在極大的不同。
已在古籍文獻研究領域打下一定基礎,又有著一身屬于年輕人的干勁與朝氣,何清湖幾乎沒有猶豫,就決定投身到這次“冒險”中去。困難接踵而至。經費不足,沒有辦公地點,也沒有任何行政資源,主編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學生——何清湖深知自己個人的學術底蘊和影響力還遠遠不夠,于是他時刻謹記抱有誠懇的態度和吃苦耐勞的精神,“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
選目、選版本、校勘、編排……在純靠人工的年代,面對如此浩大的工程,20來歲的何清湖與當時的一眾前輩老師和年輕學者共同成立了編委會,他需要積極調動這100多名專家學者,對《傳世藏書(子庫·醫部)》等進行一系列籌劃。
“每一個環節之間的難度之大,如果放到現在,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憶起當年,何清湖也不免感嘆道,這是自己做得很有勇氣的一件事,“或許就是無畏無懼,無名無利,憑著僅有的熱情和巨大的耐力,把這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完成”。
《傳世藏書(子庫 ·醫部)》系列叢書最終在1993年完成了編纂工作,成為整套“傳世藏書”最早完成的部分。它共分6大冊,17類,1700萬字,收錄有《素問》《靈樞》《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本草綱目》等重要典籍,之后,何清湖留任整套“傳世藏書”叢書編委會的編輯部主任、總編助理,繼續完成整本巨著的編輯、校對、出版。
中醫學“百科全書”誕生:
“中華醫書集成”
從113本書擴充到210種書,從1700萬字到近5000萬字——從《傳世藏書(子庫 ·醫部)》到“中華醫書集成”,是何清湖實現的又一次跨越,更是中醫古籍文獻整理在規模上的一次跨越。
1995年“傳世藏書”出版以后,很快便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反響。不過,在《子庫·醫部》的發行過程中,何清湖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收錄書籍還不夠系統全面。如果說《子庫·醫部》只是屬于大型古籍整理工程中的一個小部分,那么在自己的垂直專業領域,何清湖自然有著對更大規模的中醫古籍文獻整理項目的向往與使命感。他再次勇擔重任,以總主編的身份組建團隊,在《傳世藏書(子庫 ·醫部)》之上仔細精選,不斷地完善書籍的選目和版本。這又是一項極其復雜的工程。
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版本,何清湖帶領團隊通過對《中國醫籍考》《宋以前醫籍考》《中國醫籍志》《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等古今目錄學類工具書的普查,參考現有中醫古籍版本研究的成果,結合國內中醫文獻研究專家的咨詢,才確定了每一種醫書的底本和參校本。
上至黃帝時代、下至民國時期,最終編成的“中華醫書集成”近5000萬字,系中華五千年中醫經典之薈萃,其匯編有歷代著名醫學典籍210余種的出版篇幅,在中醫歷史上規模最大。
不僅規模大,“中華醫書集成”兼具目錄學與叢書雙重功能,就像一套中醫學的“百科全書”,何清湖不無驕傲地說:“無論從選目、版本的選擇和校勘的質量與編排的質量,甚至是導讀的內容,‘中華醫書集成’可以算是中醫歷史上最好的叢書。”

何清湖主編的部分著作。
問道經典,更為“你我他”所用
古籍保護、文獻研究與整理,聽上去像是在做一種高深、枯燥又重復的書面文字工作,形成的一本本令人敬而遠之的“大部頭”,也似乎距離人們的現實生活十分遙遠。
但中醫藥的特殊性,決定了它與每個人的生命健康都息息相關,具有不容忽視的實用價值。而人之體質、病狀千千萬,其細分領域之廣博、精深,也決定了中醫在“看病”過程中所必需的學習與積累。
進入千禧年,何清湖的工作重點,漸漸開始回歸到“細而實”。他與一些專家學者開始一起琢磨,如何在匯編中醫古籍叢書的同時,進一步實現開發和利用,“我們希望能讓現代中醫更好地利用經典文獻,從而提高臨床水平與療效”。2004年,何清湖主編出版的《止痛本草》,就是一本集古今運用中藥止痛藥理論、臨床和實驗研究成果的專著。書中收載止痛中藥839種,附止痛方劑2321首。2016年出版的“中華傳世醫書”大型叢書,則按中醫學科分為醫經類、傷寒類、外科類、傷科類、婦科類、兒科類、五官科類、針灸類等17類,涵蓋了現代中醫學的全部學科。
2013年,由何清湖總主編的《中醫古籍必讀經典》出版。中醫典籍汗牛充棟,如何體現“必讀”二字,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何清湖認為,必讀、精讀的經典文獻標準應該有3點:“一是學術創新,二是臨床實用,三是學科代表性。”
以此為標準,該叢書選取了每一位中醫臨床醫師在工作中必讀的20冊中醫古籍圖書,是學術界公認的研習中醫歷年來經典學術專著的最佳版本。翻開其中收錄的元朝《丹溪心法》,其中不乏經驗秘方,如治“胸膈痞滿,停滯飲食,單用山楂一味藥”,至今為臨床所用。既注重著作的歷史影響、學術價值,更兼具實用性和普適性,是以上中醫古籍叢書的共通點,體現出了一種現代式的“經世致用”思維。
此外,何清湖還擔任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藥古籍文獻和特色技術傳承專項”課題下多個項目的主持人,以中醫優勢病種——黃疸、鼻鼽等作為研究對象,對春秋戰國時期到民國時期的相關古籍文獻,從源到流對理、法、方、藥進行全面梳理和挖掘,并正在持續參與一個“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框架下組織實施的集保存、傳承、整理、利用為一體的中醫藥古籍再生性保護項目——2012年啟動的“中華醫藏”項目,何清湖在其中擔任“中華醫藏”診法2( 30種)( 2020年)項目主持人。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醫藥學專科叢書,“中華醫藏”從我國現存醫藥古籍文獻中遴選出兼具學術、版本和實用價值的中醫古籍2000余種,還收錄有民族醫藥代表性著作以及從海外回歸的珍貴醫藥典籍,是繼“佛藏”“道藏”“儒藏”之后,又一項系統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的重大基礎性學術建設工程。
挖掘馬王堆醫學文化“精氣神”
20世紀70年代,在位于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東郊4000米處的瀏陽河旁,一個考古發現震驚世人——馬王堆漢墓。
其中三號墓出土的醫書共有14種,分別書寫在大小不同的5張帛和200支竹木簡上,總字數有3萬字左右,既囊括中國最早的醫方書、最早的經絡學和脈學著作、最早的養生學和婦產科學文獻,又含有中華最古老的氣功導引秘笈《導引圖》,充分展現了我國先秦西漢時期的重大醫學成就。
“馬王堆醫書所具有的醫學肇源之地位、文獻價值之卓越,值得深入研究。”何清湖說道,其在湖湘文化遺產、中醫醫史文獻、中醫文化、文化傳播、甚至國際跨文化傳播領域都顯現出其獨具魅力的學術和產業開發特色、優勢和價值。
何清湖尤其注意到,馬王堆醫學文化在內容上重視“精、氣、神”的養生思想,對現代養生保健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馬王堆醫學文化,需要被推向世人。抱著這樣的信念,何清湖于2009年編著出版了《馬王堆古漢養生大講堂》,獲得中華中醫藥學會科學技術獎二等獎以及湖南省優秀科普作品獎,并在2014年參與主編《馬王堆醫方釋義》。
在成果轉化方面,除了養生保健食品“古漢養生精”,湖南省博物館也在陸續開發香囊、香皂、藥枕等多種相關文創產品,其中何清湖聯合省博物館開發的“馬王堆養生文化及養生藥枕的開發應用研究”獲得湖南省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
但何清湖還是覺得不夠,“研究、開發、宣傳的力度、廣度和深度都還不夠。”于是他開始廣泛呼吁加快推動馬王堆醫學文化研究與轉化,并充分利用自己湖南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在2019年與2022年先后提交了相關政協提案。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快古籍資源轉化利用”。時機正好,在推動中醫古籍文獻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方向上,何清湖更加堅定了信心,將會繼續致力于馬王堆醫書系列的研究創新與傳播轉化。
“中醫不只是防病治病的知識體系,它也是一種文化,而文獻是它的基礎載體。”何清湖認為,中醫藥文化與中華優秀文化有著共同的精神密碼。
光陰流轉,千年一瞬,當一部部中醫古籍被拂去塵灰,中醫藥文化的脈絡與內涵重現世人眼前。無數先人嘔心瀝血得出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智慧,與何清湖這樣一群人身上深厚的學術底蘊及“敢為人先”的精神底蘊,穿越千年,在此刻交匯。路漫漫其修遠兮,然中醫藥文化之“精氣神”,因始終有人前仆后繼,終將生生不息。
本文原載于《文史博覽·人物》2023年第3期
文 | 政協融媒記者 廖宇虹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均為采集網絡資源。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可聯系本站刪除。